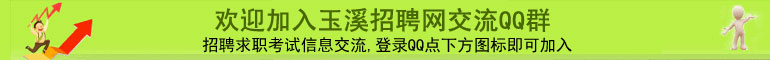劉某原系天明公司員工,雙方簽署了勞動合同,其中約定了保密及競業限制期限為勞動合同有效期內及勞動合同終止或解除后一年,并對競業限制的范圍及補償金支付進行了約定。雙方于2017年9月20日解除勞動合同,離職交接單約定如劉某收到公司發出的《競業限制補償金通知》,則須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否則,天明公司無需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劉某亦無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2017年11月30日,天明公司向劉某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劉某離職后需要履行雙方《勞動合同》中約定的競業限制義務,并單方確定競業限制期限為6個月,現天明公司要求劉某繼續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并支付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違約金,返還已經支付的補償金。
案件審理過程中,劉某主張其離職時,天明公司未向其發出《競業限制補償金通知》,故其無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
來源:北京市海淀區法院2024年5月發布8件勞動爭議典型案例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簽署的《離職交接單》明確將天明公司是否向劉某發出《競業限制補償金通知》,作為確認劉某是否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的條件。天明公司并未在劉某離職時向其發送《競業限制補償金通知》要求其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則劉某無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天明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向劉某發送《競業限制補償金通知》明顯超過合理期限,對劉某不產生約束力。
競業限制是指負有特定義務的員工在任職期間或者離開崗位后一定期間內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的企業同類的產品或業務。競業限制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用人單位商業秘密的同時,由用人單位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以平衡對勞動者的自主擇業權造成的影響。鑒于競業限制義務系對勞動者自主擇業權利的限制,為保障權利義務的確定性,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以用人單位在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時向勞動者履行告知義務作為生效條件的,用人單位應當在約定期限內通知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否則將導致勞動者的權利義務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權利嚴重失衡。因此,如用人單位未在約定期限履行通知義務,則視為該生效條件未成就,勞動者無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