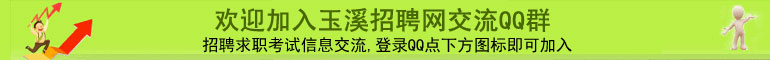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如何區分?
文章來源:勞動法庫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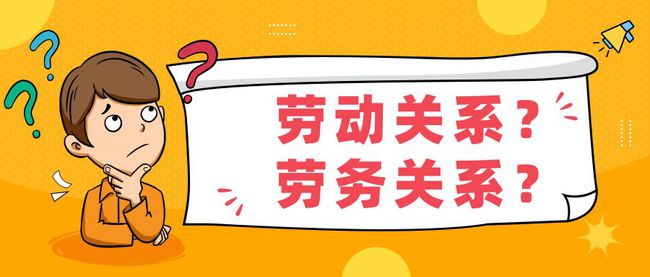
陸勇經人介紹于2011年6月進入天山公司,公司提供車輛,陸勇負責駕駛拉貨。
2022年3月10日,公司(甲方)與陸勇(乙方)簽訂了一份《勞務合同書》,合同主要內容有:
第一條 本合同期限自2022年3月10日至2022年10月31日止,合同期滿,雙方不持異議繼續順延。
第三條 乙方提供勞務的方式為按實際毛利提成發放勞務費。
第五條 甲方按現行運輸勞務標準提成向乙方支付勞務費,甲方支付勞務費為每月20日。乙方勞務費數額以甲方當月結算為準。
第六條 憑勞務發票到甲方結算勞務費,甲方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第十條 乙方同意醫療費用自理,醫療期內甲方不支付勞務費。
2022年4月23日,陸勇駕車卸完貨后返回途中,突發疾病身亡。陸勇的社會保險繳納單位為新疆建設兵團某師八十七團。
2022年6月7日,陸勇妻子孫妮申請仲裁要求確認陸勇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2022年7月30日,仲裁委裁決陸勇與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22年4月23日期間不存在勞動關系。
孫妮不服,提起訴訟。
一審判決:陸勇領取勞動報酬是按運輸勞務標準提成發放,按勞務合同的約定履行,雙方屬勞務關系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為陸勇與公司之間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
勞動關系是指機關、企業、事業、社會團體、個體經濟組織和勞動者之間,依照勞動法的規定簽訂勞動合同,使勞動者成為用人單位的成員,接受用人單位的管理,從事用人單位指定的工作,并獲取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所產生的法律關系。
勞務關系是指勞動者為被服務對象提供特定的勞動服務,被服務方依約支付報酬所產生的法律關系。勞務關系的特點是雙方為平等主體,提供的勞動內容具有特定性,雙方均按照約定行使權利承擔義務,雙方主體之間只存在財產關系,彼此之間無從屬性,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
本案中,從《勞務合同書》內容來看,該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按照實際毛利提成發放勞務費,勞務費數額以公司當月結算為準,每月20日支付勞務費。雙方對工作時間、基本工資、福利待遇等未作約定。從孫妮提供的銀行卡交易明細清單及收入納稅明細來看,也可以證明陸勇領取勞動報酬是按照運輸勞務標準提成發放,每月領取的數額不等,沒有提供勞務,當月則沒有收入,由此可以說明雙方在現實中也是按照勞務合同的約定履行的,故從上述事實及合同的內容可確定雙方屬于勞務關系。
至于孫妮提出的公司將陸勇納入職工核酸檢測名單、公司通訊錄及工作微信群,并為其提供了出入證、宿舍、工服等,系公司為履行勞務合同提供的保障方式,上述情況及證據不能證明其與公司存在勞動管理關系,亦不能推翻雙方已按照勞務合同內容實際履行的事實。故對孫妮的訴訟請求,該院不予支持。
孫妮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雙方之間符合建立勞動關系的構成要件,不能繳納社保不影響雙方之間建立勞動關系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陸勇與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二、陸勇系八十七團的職工是否能夠阻卻雙方勞動關系的建立。
針對第一個焦點問題,本案需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本院對此分析如下:
一、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別。
(一)勞動關系的特點。
勞動關系,就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一方(勞動者)將自己的勞動力有償交給另一方(用人單位)使用,勞動者人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用人單位的控制,勞動關系呈現人身關系的特征,進而成為一種隸屬主體間的以指揮和服從為特征的管理關系。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的管理與支配的權力體現在“從屬性”,此也是勞動關系與一般的民事關系最基本的區別,該從屬性主要分為人格上的從屬性及經濟上的從屬性。
人格上的從屬性主要指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指示服從的義務,表現為:
(1)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地點和業務內容具有廣泛的指示權;
(2)勞動者成為用人單位組織中的一員,必須服從用人單位組織中的內部勞動規則,即必須遵守本單位的規章制度;
(3)勞動者有接受用人單位的檢查以及接受合理制裁的義務。
經濟從屬性主要表現為:
(1)生產工具或器械由用人單位所有,原料由用人單位供給;
(2)勞動者的工作是作為用人單位所經營的事業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勞動者是為用人單位的事業提供勞動而不是為自己提供勞動;
(3)責任與危險負擔由雇主負責。
因此“事實優先”原則對于判斷勞動關系是否存在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不管雙方當事人是否訂立合同,或以何種名義訂立合同,主要考察的應是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否具有勞動關系的特點,而不能拘泥于各方或雙方如何描述這種關系。
(二)勞務關系的特點。
所謂勞務關系是勞動者與用工者根據口頭或書而約定,由勞動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服務,用工者依約向勞動者支付勞務報酬的一種有償服務的法律關系。它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平等主體之間就勞務事項進行等價交換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經濟關系,各方之間沒有隸屬性,沒有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關系,勞務的提供者自主管理,自由支配勞動力,提供勞務的一方自行承擔風險。
(三)勞務關系與勞動關系的區別。
勞務關系與勞動關系的區別主要有四點:
第一,當事人地位不同。前者當事人之間無組織、隸屬關系,地位平等。后者當事人之間存在隸屬關系,勞動提供方是接受方的組織成員。
第二,標的不同。前者的標的是物化或非物化的勞動成果,后者的標的是勞動力的使用過程。
第三,風險責任不同。前者由勞務提供方自擔風險,后者由勞動接受方承擔勞動過程中的風險。
第四,勞動報酬性質不同。前者勞務報酬與商品交換中的價款具有同樣性質,遵循等價有償規則,通常由勞務接受方一次性支付或分多次支付。后者勞動報酬是生活消費品的一種分配形式,遵循按勞分配原則,由勞動接受方持續、定期支付。
二、本案中陸勇與公司之間系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
根據前述對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分析,結合本案查明的事實,陸勇與公司應當被認定為勞動關系,理由如下:
雖然本案中公司提供了與陸勇之間簽訂的勞務合同,但是認定雙方之間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應當通過雙方的行為所產生的權利義務來確認。
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本案中,第一,雙方之間符合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
第二,陸勇自2011年6月直至2022年4月其去世一直在公司從事駕駛員工作,持續時間近11年,結合其2005年起的銀行轉賬記錄,可見其雖然每年從事的勞動時間有長有短,但其領取報酬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和持續性,還是區別于勞務關系一次性、臨時性、短期性的特點,陸勇負責運輸粉煤灰,該工作也屬于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公司以陸勇完成的工作量為其支付勞動報酬,屬于按勞分配的范疇,且陸勇的相關待遇與簽訂勞動合同的員工并無區別。
陸勇領取工資、維穩費、高溫補貼、報銷差旅費、進入公司微信工作群、公司為陸勇提供宿舍等事宜均是公司對其工作具有一定安排、指示和管理的體現,且陸勇在所謂勞務合同期限內并不能隨意決定其是否提供勞動,不具有勞務關系中自由支配勞動力的特點,因此可以認定陸勇與公司之間已具有人身隸屬性的特點;
第三,陸勇系以公司名義對外提供勞動,并且陸勇還領取了公司的工作服、工作證等,其勞動所產生的風險也由公司進行負擔。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雙方之間符合建立勞動關系的構成要件,公司認為陸勇簽訂的勞務合同即雙方之間不屬于勞動關系的抗辯理由與實際不符,本院對此不予采信。
針對第二個焦點問題,陸勇系八十七團的職工是否能夠阻卻雙方勞動關系的建立。
首先,根據查明的事實,陸勇系八十七團職工,享有職工身份地,八十七團為其繳納了各項社會保險,其與八十七團之間屬全日制勞動關系,并在其為公司提供勞動期間一直存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企業停薪留職人員、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內退人員、下崗待崗人員以及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人員,因與新的用人單位發生用工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按勞動關系處理。”陸勇雖不屬于前述情形,但前述司法解釋的規定說明目前我國勞動法律、法規并未禁止雙重勞動關系的建立,因此陸勇系八十七團職工的事實并不能影響本案中陸勇與公司之間建立勞動關系,對此本院予以確認。
其次,勞動者同時建立一個以上勞動合同法意義上的完整全日制勞動關系沒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據。
勞動部《關于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若干問題的通知》第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職工時應查驗終止、解除勞動合同證明,以及其他能證明該職工與任何用人單位不存在勞動關系的憑證,方可與其簽訂勞動合同。”由此可見,勞動者與兩個用人單位建立全日制勞動法律關系,在法律上有一定阻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第四項“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單位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這一規定也恰恰從反證了同一勞動者只能與一個用人單位建立全日制勞動關系。
本案中,陸勇系八十七團職工,與八十七團屬全日制勞動關系,其與公司之間建立的新勞動關系與原勞動關系存在較大區別,在原勞動關系未解除或終止的情形下,公司無法為其繳納社會保險及辦理退休養老手續。若八十七團需要職工必須履行的職責時,可隨時通知陸勇回八十七團上崗。上述因素導致第二份工作形成的勞動關系隨時可能解除或終止,具有不穩定性,故盡管陸勇與公司之間可以認定形成勞動關系,但其只能享有獲得報酬、勞動保護及工傷保險等有限勞動者權利,是權利限制性勞動關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全日制勞動關系,應當認定為與非全日制用工相類似的特殊形態的勞動關系。
第三,因公司對陸勇的管理完全符合勞動關系的要件,不能繳納社保不影響雙方之間建立勞動關系,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第13號令《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職工(包括非全日制從業人員)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用人單位同時就業的,各用人單位應當分別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發生工傷,由職工受到傷害時工作的單位依法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由此可見,工傷保險是兩個用人單位可以分別繳納的,此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沖突,故公司認為無法繳納社保就不存在勞動關系的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信。
綜上,二審撤銷一審判決;確認陸勇與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22年4月23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
案號:(2023)新40民終645號(當事人系化名)